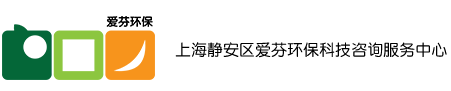

上一期聊下来,我们三个有一种共识——垃圾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,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我们不仅在聊垃圾分类本身,也是通过垃圾进一步理解它背后的城市化发展、人与环境以及人与物彼此建构的关系。
其实垃圾并不是突然成为一个紧急问题的,是经过不同的历史阶段,慢慢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挑战。中国在1950年代有一套循环回收体系的,很多老一辈的国人一直在践行“物尽其用”的生活哲学。今天再去说垃圾分类,面对的是新的人群、新的局面。
那么从上海的实践经验出发,中国的城市是怎样推行垃圾分类的呢?
上海的实践经验
马晓璐(爱芬环保资深讲师和项目顾问):
2019年1月底,上海人大通过了立法,确定实施时间是7月1号,我们后来听上海市一位领导讲立法过程,其实一般一个法律通过后,最多两三个月就要实施,唯独垃圾分类的立法给了很长时间。
那位市领导表示,尽管去年5月,真正做得好的小区还很少,但它们为法律的制定提供了事实依据,可以去说服人大代表。因为人大代表也会质疑,出台法律了,上海市民就会好好分类吗?
爱芬认为,垃圾分类做得好,一定是小区居民参与多,一般要百分之七八十的居民都会分类才行。我们从2012年开始做垃圾分类,推动过程是很难的,因为相关方太多了。不像关爱老年人,有特定的人群和需求。但大家自身没有对分类垃圾的需求。在2019年前,我们跑社区的感觉是,在夹缝中生存。
但2019年,上海要求所有部门,不管跟垃圾分类有没有关系,都要参与。
郑圆:
全社会联动?
马晓璐:
对,政府真的是要求所有部门投入。上海在2019年5月到7月,推进非常快,因为那时是有底气的。一是垃圾分类的后端从2012年开始逐步建设;二是有了成功经验。我记得2014年时,在老静安区一个街道,他们的策略是第一年先选出5个小区做试点,第二年再选出10个小区做试点。从那时起,我们也参与过政府组织的多方讨论会。
郑圆:
爱芬是一个很先锋的垃圾分类组织,还有没有其他组织呢?
马晓璐:
之前,垃圾分类太小众而没有钱投入,政府的脚步也相对较慢,更多的资源、资金集中在自己手里。在2012年到2013年,爱芬环保主要通过申请宣传活动类经费推动社区垃圾分类工作,2014年开始与主管部门建立直接合作,提供垃圾分类服务专项经费。到2014年,上海整个步调变大,政府财政预算也变大了,就有很多人进来。现在市场化了,特别是2019年,据说每天都有几百家跟垃圾分类有关的公司注册。政府采购有几块。一块是前端的宣传教育,像社会组织、小公司都会来竞标。还有就是背后的运输、技术,像互联网技术、分类收运车等等。
郑圆:
我们的社区在北京东城区,政府相应的专项资金分配设计得特别细,按每家每户算。比如,一个街道有15000多户,每户是20元,其中12元是让居委会或相关单位雇佣垃圾分拣和收运公司,8元用来做宣传。
马晓璐:

垃圾分类是推动社会参与的契机
冯婧(澎湃新闻首席编辑):
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教授做了一个总结:“日本的垃圾分类靠的是国民的素质,德国的垃圾分类靠的是企业的责任,而中国的垃圾分类可能靠的是社区。”这就把上海2019年做的垃圾分类和从2014年开始推的社区治理联系到一起了。因为我们去很多社区时,就会听到“垃圾分类变成了检验社区治理成果的一个方法。”
郑圆:
垃圾分类还是检验社会参与、社会各环节如何配合的一个标杆。
马晓璐:
但是很遗憾,大部分城市的操作方法并不是朝这个角度做的。
冯婧:
因为碰巧我这两年都在关注社区。去年5月之后,再进到社区里,就看到他们都在做跟垃圾分类相关的事情。那时你才有一点感觉,社区是推动垃圾分类的一线。
最重要的是让居民自己去分,不是别人来帮你分。当看到有些地方花钱让别人来分,或者让志愿者来分,我们就觉得很可惜,没有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去探索社区治理。其实在一个完美的案例里,一个社区如果可以把垃圾分类做好,社区治理也可以做好。
郑圆:
爱芬参与的效果好的案例里也存在这种良性互动?
马晓璐:
对,爱芬环保的创始人是从探索公民社会的土壤里长出来的,策略围绕的是培育大家的环保意识,比如为自己的垃圾负责。刚开始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跟社区自治有关系。以前居委会、物业、业委会各干各的,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,我们会把这些人都叫来,包括保洁员,大家共同讨论。之后,社区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能力更强了,志愿者的行动也不再被动。我们才意识到,社会参与式的方法促成了这么多改变。这也带动了爱芬的价值观和工作流程。
但这套方法很慢,我们介入一个小区,重新去看管理机制,要打破原有的工作思路,拔高他们的工作能力。这就是爱芬提出的“培育和赋能”,可能花6-8个月把1个小区培育出来。在这个过程中,要挖掘出不错的志愿者,再培育志愿者团队的领导人,整个过程很长,但出来的效果很好。
在一些街道,我们一年可能会去社区30-50次,但后来他们被外包公司服务,一年就去两次,按次算钱,搞一次活动,搞一次培训就结束了。所以,爱芬模式和“大跃进式”的进度要求以及折算经济价值的思路,完全不在一个维度。
冯婧:
爱芬的方法就是做社区治理的方法。最重要是建立社区里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,让大家彼此有基本的信任。如果社区里没有任何基础,居委会突然去敲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居民家的门,说明天要垃圾分类,你觉得这个人会分吗?连认识都不认识,怎么推动?所以要有社区治理的基础,有一定的关系网络后,垃圾分类才会好推进。
马晓璐:
爱芬和政府的合作很密切,也算是给政府论证了这条路。
冯婧:
如果可以通过垃圾分类的契机,让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的关系变得好一点,附加值是很大的。
郑圆:
北京的社区也很复杂,我们在老城区胡同里,动员公民参与这还是比较容易的,老年人比较多,相对是熟人社区。反而感觉居委会的工作压力不小,比如他们被要求厨余垃圾的分出率要到18%。再比如做垃圾分类宣传,是跟我们团队合作,把宣传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一些。各个社区间是有评比的,社区能不能做出亮点来很关键。
马晓璐:
为什么政府会选择企业服务,因为好管理,可以很快出效果。我们作为第三方去小区沟通,要很快判断物业、居委会的能力情况和意愿,缺什么能力,有什么矛盾。有的小区是居委会能力弱,有的小区是物业跟大家矛盾很深,我们要去考察每个小区的情况,这是很难很长的过程。
郑圆:
北京也是,平房区和楼房区还不一样。
马晓璐:
上海也是,每个小区会说,我们小区是最特殊的小区,可能每个城市也会这么说,所以2019年上海政府提的是“一小区一方案”。
郑圆:
垃圾分类也是一个发现问题的过程:上传下达和自下而上的互动做得好不好?是不是在做公民参与的基础性工作?
马晓璐:
我们观察到,有的小区居民动员做得不好,会找很多原因,比如出租户多,人口数多,而且还觉得大家都没有做好,也不会怎么样。虽然有压力,但不会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好。
冯婧:

垃圾分类与个体的关系
郑圆:
为什么垃圾分类会让社会参与如此显影?是不是因为,每个人都是政策能不能成功落实的利益相关方,没有“我”的参与,这事就真的推不动。
马晓璐:
在上海,我们觉得永远要查缺补漏。有一次我去上门宣传,是一个小男孩开门,我说你家长在吗,给你们讲一下垃圾分类。然后小男孩说,妈妈你快过来,那天跟你说垃圾分类,你还不相信我。
郑圆:
其实垃圾分类也有一些来自民间的非议,大家会抱怨,太强制了、太武断了,凭什么突然要全民参与?但今天听你们聊,推动垃圾分类本身没有什么问题,问题是不能突然开始,可能要对公民社会的建设、社会组织的活力,以及各个环节之间的沟通有个考评。
冯婧:
不是说今年想推就能推下去。上海是做了很多年的准备,才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推下去。很多人会说,“我在家分好了,看到你们后来又混在一起!”对于这个质疑,以前政府可能真的说不清楚,而一旦建好了,就可以更好地回应。如果居民看到问题,可以去投诉,行使一个公民的监督权。
郑圆:
我觉得爱芬有一个社会创新点:政策落实想一步到位是不行的,需要有人从中协调,去做润物细无声的培育和陪伴,进而试验新方法。
马晓璐:
是的,你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系统问题,解决需要很长的摸索过程。它不像商业世界生产产品,有明确的目标客户。我们今天面对各种社会矛盾,需要更多的人成长起来,组成社会组织,形成力量去关注和探讨问题。另外,因为政府是父母型政府,有问题了,很多居民会说这是政府的问题,不会说“我应该去做什么,我能做什么”。
现在,上海的垃圾分类基本处于常态化管理的状态,而且政府已经意识到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价值。最近,我们正在探索其他城市的模式,还是挺难的。
在中国,类似爱芬这样的环保组织很多,但政府没有垃圾分类财政预算时,大家生存得很艰难;而有钱了,社会组织也很可怜,拿不到项目经费,因为都给公司了。
发现“隐形人”
郑圆:
垃圾分类也能让人重新发现周边生活,比如拾荒者一直存在。我们受到一个艺术家的启发,广州在进行一个城市更新项目,改造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建筑垃圾,包括原先建筑里的生活废品,艺术家就慢慢摸索出一个拾荒者链条。这启发我们去北京的社区里观察拾荒者,我们发现拾荒者不是一个模糊的群体。
比如我们社区有一对夫妇,他们在这个片区已经10多年了,每天下午4点定时出现。他们手机里有大量附近居民和小商铺的联络方式。他们的联络能力不可小觑。还有一类是游击者,不定期出现,背个大麻袋在夜间行走。还有那种老奶奶,拉着一个婴儿车,附近哪家装修,她就集中去收一波,她是生活有困难的。
很神奇的是,我家楼下有一个大姐,她是那种社区活跃分子。她有个好姐妹,儿子有精神疾病,平时会收一些废品维生。这位大姐为了帮好姐妹多赚一些钱,就联络了同楼层五六户的居民,商量能不能把废品都给她。为了让她更有尊严地拿到废品,就商量好把废品搁到楼道里的一个地方,默许她可以拿走。她这是在做社区营造啊。

马晓璐:
我们发现社区里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是老年人,他们的公共意识更强,“垃圾分类是为了子孙后代好”,真的是他们很强的信念,当然他们也会说政府要求的就应该去做。不过他们确实有时间,没有年轻人那么匆忙。
年轻人会比较极端,有环保意识的会比较好,没有环保意识的人群占比更大,觉得有没有垃圾分类无所谓。最差的可能是中年人,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。
我会关注垃圾分类落到每个人身上,怎么看这件事。凡是分类特别好的小区,去问居民,大家会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如果是分类效果不好的小区,大家会说,这是保洁员的事情、是政府的事情。
我有个艺术家朋友说,他去年回上海时,发现街上推行垃圾分类的标语和“扫黑除恶”的标语一样,他就很反感。后来我跟他解释了许多,他就理解为什么要垃圾分类了。
当你很强势地去宣传,大家的负面情绪和不认可是排在前面的。但垃圾分类这件事其实更关系到年轻人的未来。当其中存在误解时,我就觉得特别可惜。
冯婧:
可以说垃圾分类是个很强势的政策,但如果可以真的理解到它后面的问题,大家一定会觉得很重要。这个是超越国家的行为,这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。所以媒体在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工作,可以让大家看到彼此。一方面,民主要相信政府会完善末端处理;另一方面,政府也要相信民众可以自己做好分类。如果可以通过垃圾分类这件事,彼此都有一定的成长,那么垃圾分类就做了超越处理垃圾的事情。
其实,这样的契机并不多,关键是大家能不能利用好这个契机。如果你意识不到背后的价值,可能就会用很粗暴的、短平快的方式来做垃圾分类,就只能说,很可惜,你又浪费了一次可以改善这个社会的机会。
解锁社区无废生活的想象力

我们通过创意调研工作坊把居民聚集起来,有点模拟胡同杂院里的状态,大家组队讨论。小组之间也可以彼此激励和比拼。不过让大家投票哪个小组的表现最好,居民都投自己组。
两次工作访中,我们受益很大,居民们尤其是老年居民,生活智慧真的了不得。有的居民认为,无废就是一切从简;有的居民认为,垃圾分类的核心就是物尽其用。这些理念都深入他们的生活哲学里,并且他们一直在实践——海鲜产品泡沫包装盒可以种花、买菜的塑料袋留着装垃圾。
而且他们反复强调,这事应该多跟年轻人说,我们是从艰苦朴素的年代过来的,你让我不勤俭节约都难。当然,有的胡同居民会囤积东西占用公共空间。
我还发现了“废”的文化。很多老年人家里柜子里的布料、粮票等,都有人的回忆和感情,你说这是“废”吗?很难讲。所以我们想重新定义“废”和“垃圾”,让物跟人产生关系。也想让老年人和年轻人互动起来。
后来,我们做了无废空间站的艺术创想计划和展览,请不同专业领域的年轻人一起探讨。有的方案提到,无废空间站不应该是一个固定地点,不需要新建空间,可以在社区范围内有一个流动性的认证。
还有一个创想叫旅行者床垫。一个年轻女生提出来,社区里有很多因孩子上学搬家而产生的废弃床垫,可以收集起来做解压蹦蹦床,或者放在游乐场里面,甚至可以在复古风的咖啡馆里做椅垫。
我想,这些想法就是艺术的驱动力,既在日常生活中发展,又能让你跳出来思考。
冯婧:
在社区里面做无废城市特别好。当大家已经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,就要继续往下走,慢慢让大家去思考未来如何做无废城市。
郑圆:
我们在社区推广无废行动其实蛮难的,不只是对居民,对我们来说也很抽象——“无废”到底是什么? 跟年轻人沟通,要让年轻人跟你玩起来,一是要在机制和表达上有意思,二是可以发挥他们的职业能动性,这样他们就可以贡献独到的想法,觉得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。

郑圆:
有一次我们做活动,一个咖啡师要扔什么东西,有个阿姨就说,“别扔,我们现在提倡无废”,这让我们觉得很欣慰。通过几次工作坊的活动,居民对于“无废”这件事更有感了。
冯婧:
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达到的。垃圾分类,不是别人强迫给你的,而是你自愿做的一件事情,如果大多数人可以养成这个习惯,未来的无废城市才可能会成。
马晓璐:
会自然而然的,相当于种子都种起来了。
冯婧:

郑圆:
这又是全社会联动了,引起了很好的社会效应,让大家重视回收利用。
马晓璐:
这个一定要在地,比如说小学乐队,就要收集大家自己的东西,一起演奏时才觉得联系会更强。